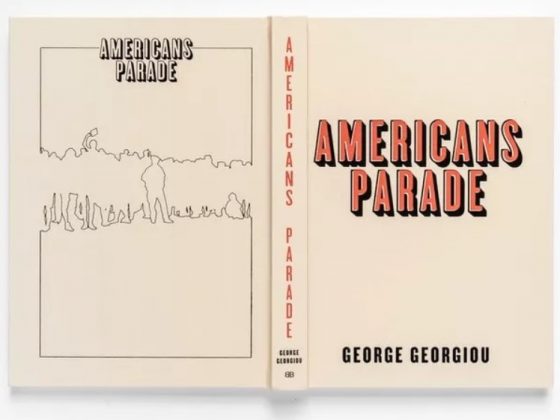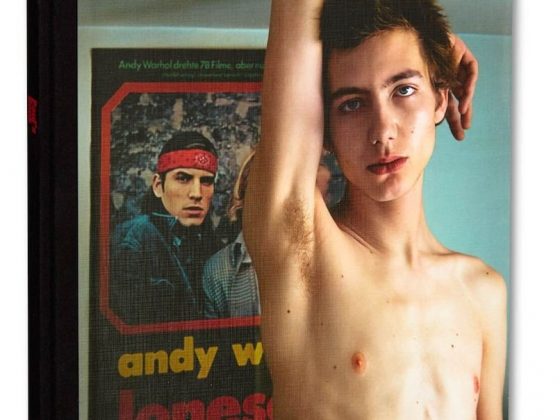Q:首先,恭喜你獲得今年的侯登科攝影獎。在這個以《生》為標題的系列中,你對生死的思考與想像是什麼?
周強:謝謝傅老師,這與我的經歷相關。9-10歲,我爺爺把我送去學“道士”(喪事法師)。從小就跟死人接觸,那時候我就知道自己也會死。另外,我做過幾年報導攝影師,見了各種重大突發事件,有一次拍攝過程中自己也差點喪命。人降生就是在為死做準備,不要對死亡抱有敵意和猜疑。
Q:慾望是一個抽象的詞彙,在用視覺來表達時,你側重在哪個層面進行視覺化?
周強:作品僅代表我個人對這個世界的感性認知。12歲那年在江邊釣魚看到的一片因放生而死的魚。十三年後,當我看到寺廟裡的放生池,這兩個毫無關聯的場景,卻在我大腦裡不謀而合。我就會拍下來轉化為我的作品,這都主觀的,感性的。讀作品的人應有自己的看法,不必按照我提供的文本信息進行解讀。


Q:《生》這個項目拍攝了多久?在這過程中,有哪些故事或畫面,是你因為一些原因而沒有拍攝,但卻是一個難忘的故事或畫面的嗎?
周強:已經拍了三年,還在持續。今年2月去了一趟北京海底世界。看了半場,白鯨、海獅、虎鯊表演。動物為了滿足人們的窺探心,被迫的做著各種動作,寄生在一個固定的空間裡。表演途中,我坐在看台上有一種莫名的不適感,然後離場。走出場館大門之後,我問自己,今天我是不是也成為了這場表演的幫兇?
Q:你的這個系列中,動物的圖像佔了一定的比重,它們在你這個系列中承載了哪部分的表達?
周強:做這個系列起初,我去動物園比較頻繁。因為我覺得那些動物都是被迫的,人們替它們做了選擇…這符合我的需要。直到看了北京海底世界動物表演後,再也不去動物園了。



Q:你的肖像部分都不是抓拍,似乎都與拍攝對象進行了交流後再擺拍而成,哪些人會作為肖像進入你的作品?你的判斷標準是以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故事,還是其他?
周強:交流只是為拍攝提供便利條件,不至於冒犯。選照片也是感性的,硬要說標準,可能會根據整組作品的氣質和圖像語言來做取捨。創作就是游離在感性與理性之間,用言語多數時候講不明白。




Q :有哪些藝術家或攝影師是你非常欣賞的?為什麼?
周強:我喜歡戴維·赫伯特·勞倫斯。他寫的小說和畫我都喜歡,因為他有一股無法描述的騷勁。欣賞的攝影師就很多了,嚴明、駱丹、塔可、須田一政、杉本博司等。喜歡他們對待藝術的誠懇和踏實。


Q :外出拍攝時,你一般都是如何度過一天的拍攝的?
周強:天亮出發,天黑找住處。走到腳底發麻就差不多天黑了。
Q :為什麼會選擇用正方形的構圖?
周強:穩重、厚實。


Q :你好像有閱讀的習慣,可以說說哪些書對你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嗎?
周強:我看書很雜,什麼都愛看一點不精。影響最大的是黑塞的小說《悉達多》,看了三遍。修行不只是僧侶的專屬,而修行有萬千種。
Q :接下來會有什麼計劃?這個系列會在其他地方展出嗎?
周強:繼續幹,希望明年有機會做展覽。




關於項目:《生》
12 歲輟學後,我無所事事遊手好閒,江邊釣魚混日。一天江面上飄來一片翻著白肚的魚兒,有些死了,有些奄奄一息苟延殘喘。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隨岸逆流而上,渡口船夫告訴我,“ 上午有人放生” 。生死與私慾,在當時並不是我關心的,我僅是好奇而已。2017 年我在一座寺廟裡看到放生池裡的烏龜在假山下曬太陽,假山上的公鴿子在尋求交配。時隔十三年,這兩個並不相干的場景在我大腦裡不謀而合。我按下快門拍下了眼前的畫面,從此開始有意識的用相機探索生存與慾望之間的關聯: 它們之間到底有怎樣的關係,又是如何影響我們的行為和思考? 慾望是由一個個肉體、介質在空間裡交織而成,看似波瀾不驚卻潛伏在現實生活中,構成了我們賴以生存的公共場域,成為具象的生活內容或世俗狀態。我遊走於城市、鄉村、山川、河流之間,用相機還原觀看。這些影像所記錄的都是它們在這片土地上的即時反應。 —— 周強
周強
1992年生於四川自貢,現居四川成都。12歲輟學,奔波於生活,2010 年接觸攝影,作品曾在巴黎、紐約、日本、柏林、北京、上海、成都等地展出。2019 第七屆侯登科紀實攝影獎、2017 年露西攝影獎 (IPA) 金獎、2018、2019 馬格南基金提名。作品被收藏於機構和個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