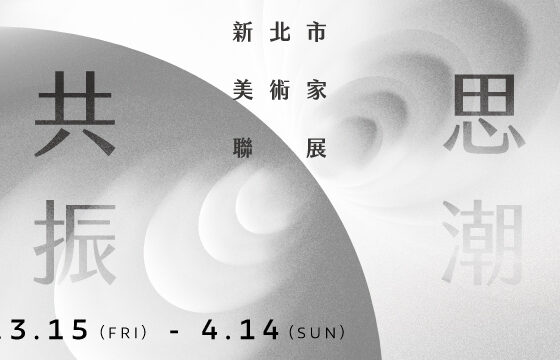Pieter Hugo生於南非,他在10歲時第一次拿起相機時,便 “被迫” 成為了一個拍攝政治的攝影師。在南非這個特殊的國家,很少有人能夠避開政治制度而創作。
他拍攝青少年、種族主義與貧困問題,這些 “老生常談” 的題材在他的鏡頭下卻是不一樣的—它們與看上去要表達的事物背道而馳。
《1994》是Hugo早期的作品,拍攝了一群在1994年後出生的少年,他們的父輩無不是在種族隔離與大屠殺中生存下來的,而作為新一代的孩子,他們的成長不可避免的沾染上了歷史的憂傷。
如今的輿論早就習慣通過這些新一代來體現平等意識,比如拍攝他們的前衛裝扮、他們的合乎時宜的理想與追求。在拍攝中,Hugo讓他們穿上自己最喜歡的衣服,女孩們穿著與大都市無異的金色裙子坐在岩石上,男孩則穿著隨意的T恤與短褲,裡著這些 “與世界一樣” 的服裝,他們直直的望著鏡頭,他們真的與世界一樣嗎?



Hugo放大著這些眼神,它們是出身、地位與身份的凝聚,是一個無法被掩蓋的事實:在歷史長河中,他們的血液還浸在漫漫的悲哀之中。


在接下來的《親戚》系列,Hugo “以身作則” 的繼續了身份的探討。
他雖出生在非洲,可他是一個白人。因為膚色,他總是不經意的穿梭游離於種族主義的外表與內裏之中,聽聞著外界不一樣的聲音,經受目光。他表面上和所有人一樣走在都市之中,而另一半的他卻生活在這個國家所殘留的殖民主義中。


Harmony Mine, Randfontein, from the series ‘Kin’, 2012
《鬣狗和人》是他的引起最大關注的作品,講述了一群尼日利亞的馴獸師,他們靠鬣狗、猴子的表演賺錢,這是他們的祖輩的傳統,更是唯一的生計。


這並不符合外界的價值觀,由於《鬣狗和人》的發表,國際動物權益組織開始介入這個群體,他們要為這些可憐的動物爭取應有的權利。

後來,Hugo在街上問尼日利亞當地人 “怎麼看待這些動物?” 他們沒有一個人提到 “權利”,說的盡是 “收入與生計” 。
Hugo的攝影主題一直在提出問題和偏離問題,哪個才是問題的重點呢?南非少年們的現代著裝、膚色和動物的權利,還是潺潺流淌的歷史的憂鬱、城市裏刺眼的種族主義和實實在在的貧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