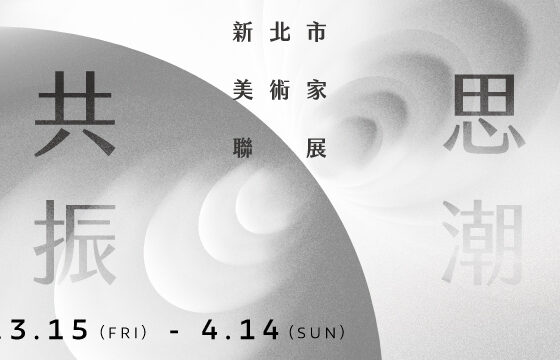2011年,Lars von Trier為觀眾們奉上了電影巨作《憂鬱症》,講述一個整日因情緒病而死氣沉沉的女人,以及一顆神秘的正向地球飛速逼近的小行星,這喻示了從心理到環境的由內而外的毀滅正在發生。
在Lars von Trier的建構下,憂鬱症成為了一種更為宏大與科幻的事物,有觀眾評價為:矯情、自大狂式的憂鬱患者。而同時,他又擬造出了一個宛如幽藍色瘡痍的情緒化世界。

Simon Kerola來自瑞典,是位20出頭的年輕人,與大家一樣,他為自己的情緒而困擾,於是他的所有作品都專注於憂鬱的自閉情緒,而他還和其他年輕人一樣,在裡面牽扯著青春的浪漫、矯情與詩意。




在一個廢棄的居所與戶外,“他” 一個人度過著剩下的日子,末日的氛圍和太陽的暖意一同拉開序幕,花朵與草的顏色蓋不住曠袤的緊閉感,鐵絲網和籬笆在濃霧中籠罩所有人的眼睛。


Simon Kerola研究著憂鬱的電影化敘事,卻承認自己還沒有搞清楚憂鬱,於是這些作品更具有個人化,還伴隨著以自我治療為目的的結局。
內心與外界的疏離感無處不在,當太陽從遠處升起,人們內心的恐懼與敬畏也油然而其,失落感與渴望同時倒影在湖泊的鏡像中。在Simon Kerola的作品與Lars von Trier電影的相似之處還在於:大自然(宏大的事物)永遠佔據著人類的主導地位。

某種程度上來說,每個人都在遺棄著自己,平常人因世界末日的來臨而患上憂鬱症,憂鬱症患者則因末日而獲得瞭解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