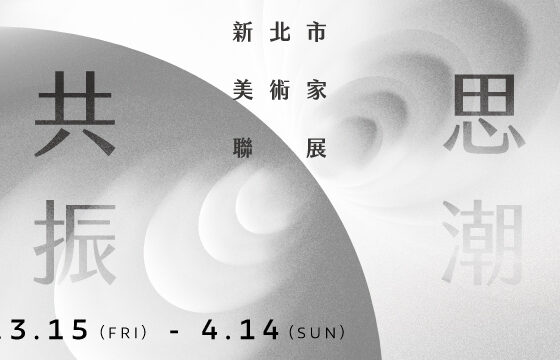1979年,Nan Goldin拍攝了《性沉溺者的歌謠》,後來她說,在那時,她是多麼的激進,因為還沒有人像她這樣創作過。而現在,人們會覺得她只是這類創作中的其中一員而已。
這段話揭示了私攝影的發展歷程,它們由實驗、先鋒的大腦創作開始,蔓延至今,已經演變為一種既定的風格。
因為私攝影這個辭彙的特殊性,它越發廣泛的進入到了各種攝影領域。它必定被囊括在寫真與私房作品中,以筱山紀信和荒木經惟為模仿對象;它出現在理光相機的論壇中,人人爭做第一百個森山大道;它還有更模糊的界限,是所有說不清楚風格與領域的代名詞。


而回溯到每一個攝影階段的最初,都不乏有一些能讓我們再次思考“私攝影”的傑出攝影師。
Francesca Woodman曾試圖用這樣的攝影救贖自己,在意大利佛羅倫斯的鄉村,在一間有鏡子的房間,她百轉千回的凝視自己的靈與肉。她的攝影嘗試來源於布勒東的小說《娜嘉》,講的是自我與 “世界上的另一個我” 的相遇,這是一個讓人感到熟悉的聯想,但Francesca Woodman的摸索是如此的鮮血淋漓,遠遠脫離了矯揉造作與無病呻吟。




還有深瀨昌久,他歡欣的拍攝妻子的裸露的背、每天在樓下的笑臉,而後在荒誕與病態之中將愛戀收場,在無盡的酒醉之中投向灰暗的天空,那如黑色星星般的烏鴉隨著飽滿的自我四處噴溢,直到乾涸。



私攝影在年輕人之中是彌漫了淡淡哀傷的自我表述,後者更甚於前者,偶有痛徹心扉的表述卻會讓人不自覺回望起一起熟悉的影子。
然而,大概正如同菲茨傑拉德在《夜色溫柔》中所說的,幾百年來,人類在這裏進行著的是一樣的青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