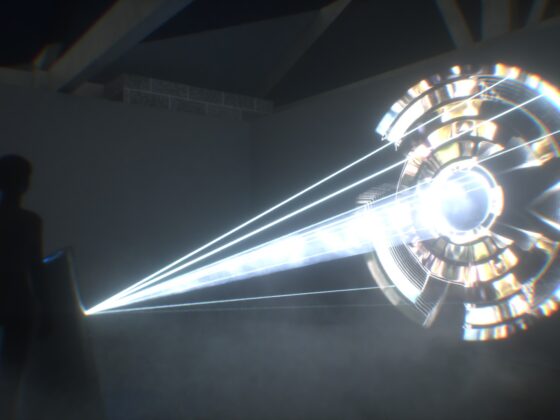Garry Winogrand 的腦中有一個高頻率工作的處理器,在見到事物動態的一瞬間,便能歷經複雜的視覺判斷,飛速地捕捉到其中最使人驚訝的畫面。
他是 60、70 年代美國最為知名的紀實攝影師之一,他與 Robert Frank 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。

在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以前,Garry Winogrand 的志向是畫家。而在邂逅攝影沒多久,他就拋棄了繪畫。後來他如此闡釋了自己的攝影:「一種能量、自大、好奇心、無知和幼稚的街頭智慧,以無紀律的姿態混合。」
1951年,Garry Winogrand參加了一個紐約攝影培訓班,彼時的他正為《體育畫報》和一些紙媒拍攝新聞,是一個絕對普通的攝影記者。在培訓班上,他去問導師:「我該用什麼相機拍照?」導師答道:「你用徠卡吧。」這位導師叫做 Alexey Brodovich,他似乎是一位徠卡專業戶,因為在此之前,推薦 Robert Frank 使用徠卡的也是他。
幾年後,Robert Frank 的攝影集《美國人》面世,Garry Winogrand 看完了《美國人》,他第一次堅定了自己的理想,不是畫家,不是記者,而是要成為紀實攝影師。
從 50 年代到 80 年代,Garry Winogrand 用一部徠卡m4 拍攝了數十萬張照片,那是另一部《美國人》。如果說 Robert Frank 是用深沉的眼睛捕捉美國「荒原」的頹敗、孤獨與感傷,那麼Garry Winogrand 就是一個奔跑在街道上的孩子,他用好奇的眼睛掃過一切,他從清晨跑到黃昏。到了夜裏,他便仔仔細細地告訴你今天的電影院是多麼地擁擠、公園長椅上坐著的一排女生穿著怎樣的裙子、一隻猴子在車上生氣、一片氣球飄舞在人們的頭頂。

Garry Winogrand 的攝影也成就了關於美國人的一部更為廣泛的傳記,他熱愛小廣角的代入感,一如他所認為的:「Be there or no photo.(你在場,照片才會誕生)」。值得一提的是,他非常討厭「街頭攝影師」這個名詞,他覺得這是一種極不恰當且毫無意義的描述。他常和 Diane Arbus 一起走在街頭,Diane Arbus 總有精確的目標,他則和 William Klein 一樣瘋狂「掃射」。









Garry Winogrand 在 60 年代後多次得到 Guggenheim 基金會的贊助,作為一名自由攝影師,他孜孜不倦地拍攝照片以及教授攝影課程。遺憾的是,他在 56 歲那年因為膽囊癌而去世,否則他還會跟隨時代繼續記錄下去。而他去世時,工作室裏還有 3 萬張未經發表的作品和幾千卷沒來得及沖洗的底片。



2018 年,導演 Sasha Waters Freyer 為 Winogrand 拍攝的紀錄片上映,片名正如同他的人生:《萬事萬物皆可攝》(All Things are Photographable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