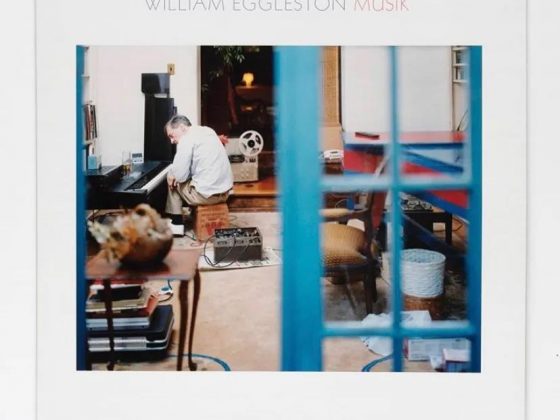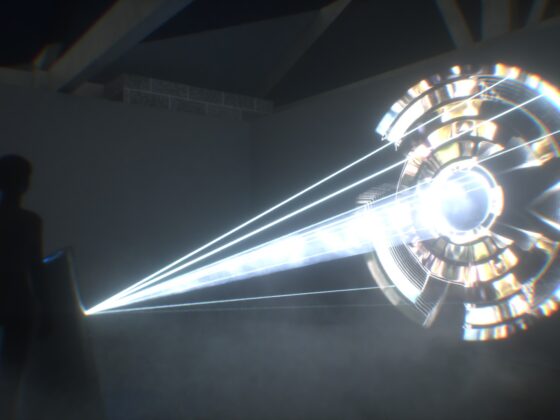關於登曼波的作品,攝影圈跟當代藝術圈討論的重點並不一樣。我聽到攝影圈的朋友都在講Wolfgang風格的問題,但是當代藝術圈對於那個框內影像其實沒有那麼大的興趣,他們比較在意那個作品在空間之中展呈的形式。這是一個老爭論了,它反映了攝影界認定框內影像仍然是攝影技藝的根本,而另外一批人卻認為攝影的技藝,或著說任何單一媒材的技藝在創作當中都不具有決定性的位置,如何調度多種媒材並與社會產生關係,才是他們在意的部分。這個分歧也影響了觀眾如何看待生命史這個問題。當代攝影當中的生命史取向是經過攝影學嚴肅的考慮。是攝影在當代藝術世界裡面為了與其他藝術相區隔,因而發展出來的一種攝影方法學。還有什麼媒材比起攝影更加的與對象相連結?還有什麼藝術比起攝影更適合從對象發展出一個計畫,然後進而深究其中對象與拍攝者自身複雜的關係。就這一點來講,這類主題性、計畫性的作品是有道理的,因為他讓攝影更像一個當代藝術中的學門。
表面上攝影圈與當代藝術圈都會討論作品當中的生命課題,但是實際上出發點卻是不同的。在意影像風格的人。會強調這個作品並非只是模仿,它是個人長期以來面對生命重要課題的結果。換言之,這些影像是生命積累而成的。真誠在此既是一種道德上的質素,同時也是一種影像上的保證。但是對於不在意或是不熟悉攝影影像風格的人而言,他們看待生命史的重點並非個人的誠意如何轉換成影像風格,而是攝影的日常性(家庭照片、生活紀錄)讓攝影介入了一個社會當中的課題。是那個抽象的關係,而非個人的真誠在藝術上有討論的意義。
我們樂觀的來看,生命史計畫銜接了攝影與當代藝術。一方面生命史的計畫保留了攝影本身的特性,譬如攝影與人接觸,攝影可以融入日常個人的生活。但是另一方面,個人生命史又可以連結到一些個人之外的議題。譬如身份認同、性別、族群等等。所以個人生命史其實一點都不個人,而是一種議題的切口。(待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