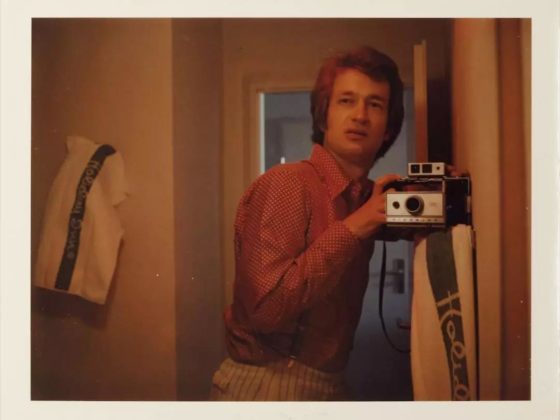作為一名建築攝影師,Fabrice Fouillet的作品力求呈現人類與其所處環境之間的關係。在其作品中,我們看到處於不同環境中的建築,在全球化的背景下,因歷史、文化而已經形成的在地風格,正在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等力量的交織下,發生著趨同性的改變。資本、權力以及作為潮流製造者的跨國建築設計公司等,正有力地參與著這種趨同化的改變。在這過程中,完成與未完成、傳統和現代建築之間,都在其所屬的特定環境下,構造出一幕幕跨文化的風景奇觀。
延續其對建築本身、建築與環境之間關係的探討,Fabrice Fouillet以“個人崇拜”為主題,展開了對世界各地巨型雕像的探索,《巨像(colosses)》系列由此而生。

在《巨像》系列中,Fabrice Fouillet有意地從宗教信仰、意識形態、民間傳說等不同維度,來豐富其關於偉人如何被紀念和呈現的表達。
Fabrice Fouillet站在一個高高的角度,以超越個人情感的客觀冷靜視角,通過豐富的採樣,對不同地點以同一視角進行反复的拍攝。這種近乎客觀和科學分析的模式,即展現了攝影敘述環境及其變化的能力,也促使觀者開始思考主宰著人與環境之間關係發展變化的背後力量。 Fabrice Fouillet以一種觀看生活模型的旁觀者視角,喚醒了我們反思自己與周遭環境關係的敏感神經。
《巨像》中,規模象徵著力量的不平等,象徵著權力和信仰等,以有形的力量加諸於普通個體的控制與規訓,同時,也凸顯了處於不均等關係中個體的脆弱,也展示了這些主宰的力量如何強行進入到我們的生活環境之中,直至成為我們的日常習慣。

因此,巨像以其人類學式的田野調查,為我們提供了個體如何被龐大的力量所影響、控制、主宰的視覺解說。其分佈在世界各地的田野調查,反應了人類這種控制與影響的共性及手法的多元。
這些巨像,如證據般觸發了我們去思考在不同歷史、文化、制度下,思想和精神所受到的影響和主動的崇拜。由此,Fabrice Fouillet以一種規模龐大的可見,為我們呈現了一種不可見。

Q & A
傅爾得:我知道您在大學期間學的是社會學和人類學,在那之後您學了攝影。什麼促使您去學的攝影,是有什麼書、電影或是藝術家等在一開始影響了您嗎?您在大學時的學習和研究對您之後的拍攝是否造成了影響?
Fabrice Fouillet:當我還在讀大學的時候,就已經知道自己想要當攝影師了。我大學非常享受社會學,同時也很著迷於攝影。那時我的拍攝主題非常簡單,常常拍身邊的周遭,尤其愛拍風景。那時我正住在法國的波爾多區,那兒的葡萄園是一個探索的好地方。之後,我發現了大師沃克·伊文思(Walker Evans ),就開始對日常的城市建築和景觀產生了興趣。布列松(Henry Cartier Bresson )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的攝影品味。但我想,自己對影像的喜愛可能真正來自於1950到60年代的意大利電影,高中時我曾研究過電影,導演費里尼(Fellini)、維斯康蒂(Visconti)、安東尼奧尼(Antonioni)等,都在很大程度上喚醒了我的藝術感知。
傅爾得:我發現在拍這些巨型雕塑時,您都站在了一個較高的地方。作為建築攝影師,拍攝中您遇到的挑戰主要是什麼?相比拍室內和室外,您認為哪一個更具挑戰性,或者更費時?
Fabrice Fouillet:建築攝影有時候很有挑戰性,遇到的限制也很多。天氣是一個長期性的限制,它決定了光線的質量,如果天氣很糟糕的話,就要看看怎麼來處理。建築物周圍的環境、城市公共設施、缺少後退的空間等等,都可能成為棘手或複雜的問題。我喜歡將建築物在其所處的環境中以整體來呈現,從高處拍總是很有趣,但要到達高處的視角卻總是很難。我以前碰到這種情況時,大多時候審批就要等好幾天。而如今,無人機就能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,但新的問題是,有很多地方不可以用無人機。對我來講,相對於情況往往並不是太複雜的室內拍攝來講,拍室外要更費時一些。拍室外要將建築物周圍的環境都勘探一番,甚至是離所拍建築很遠的地方都要弄清楚,這些都能花掉很多的時間和精力。但拍室內也有其他的限制,比如,人造光源會顯得很難看,而室內狹小的地方,哪怕用廣角鏡頭也不一定拍得了。但是我想,重要的是,約束與品質是密切相關的,如果你不想受太多限制也總是可以的,但那就很容易出壞片子。
傅爾得:是什麼促使了您決定去拍攝《巨像(colosses)》這個系列?
Fabrice Fouillet:我那時一直在研究世上的偉人大致都是如何被呈現的,我想要圍繞著個人崇拜來展開一個計劃,而對我來講,雕塑似乎是首要的探索。在研究的過程中,我遇到了一個讓人難以置信的巨型雕像,就是我在日本看到的仙台大觀音像,這座巨大的白色雕像位於城市的中央,這實在讓我感到不可思議,我很快就看到了我的拍攝主題。這推動了我的研究,以估計拍攝這個系列的興趣和可行性。

傅爾得:為了拍這個系列,您到過世界很多地方,從烏克蘭到俄羅斯,從中國到日本,從印尼到塞內加爾,這個項目所積累的東西似乎已遠遠超過了雕像本身,它更深層地反應了這些國家的歷史、宗教、政治、文化等,您為什麼選擇這些雕像呢?從照片敘事的角度看,您希望觀眾能從這些照片中獲得什麼?
Fabrice Fouillet:雕塑的大小自然是選擇的標準之一,即便在照片上看來,那些最大的雕塑並不比那些適度大小的更有趣。最終,我偏向去表現雕像的象徵性以及它們是如何被理想化的。在塞內加爾國達喀爾的“非洲文藝復興”或俄羅斯伏爾加格勒的“祖國在召喚”等雕像,都是一定要去拍的,因為這些雕像傳達了強烈而堅定的意識形態。我想與這些雕像保持一定的距離,以便看觀察它們是如何以那樣不成比例的大小融入到周圍環境中的。相比於巨型雕像的象徵性和其對巨大的強調,它不相稱的比例其實多指人的渺小。紀念性也指政治或宗教的力量,它們本身與其像徵和教育的特性是不可分的。從社會的角度來看,這些雕塑都有一個假定的功能,即它們都將自己強加於所有人的眼睛。

傅爾得:作為一種攝影理念或是一種持續吸引您的形式,您是怎麼理解社會景觀攝影的?
Fabrice Fouillet:社會景觀以理解空間呈現的方式引發了我的興趣。我認為,不管這個空間被稱為社會與否,它都可以觸發對空間形成變化過程的思考。今天,景觀正持續地發生著變化,這已成為空間規劃政策的中心因素,這些轉變觀察起來總是很有趣,攝影也是某個地區興衰變化的一種見證。社會景觀正如圍繞著一個人的畫像,它即是記錄性的也是有美感的,同時又與政治議題及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角色密切相關。
傅爾得:為了完成這個系列,您到過中國的很多地方,如您在山西運城拍過關羽雕像,在佛山拍過觀音雕像,您是怎麼選擇中國的這些地點的,可以說說原因嗎?
Fabrice Fouillet:在中國有很多紀念雕像,我也很想多拍一些。我是在網上做調查時,發現了山西運城的關羽雕像,當時立刻覺得它應該被列到我的拍攝名單中。關羽是我最喜歡的雕像之一,我發現它既美麗又耐人尋味,我也喜歡它的顏色。但靠近這尊雕像還是很有挑戰性的,它有一點點孤立,但這也增添了它的魅力。關羽的表情讓人印象深刻,且博人尊敬。拍這尊雕像是一定要的,因為它不涉及宗教領域,且它完全符合我所尋找的理想類型。在佛山的觀音像是一個宗教例子,雕像看上去有經典的美感,但我一直都被它的規模及其在寺廟中的位置所吸引,這是一尊極好的宗教代表性例子。

傅爾得:您的建築攝影更像是探索人和其生活環境之間關係的社會景觀,您怎麼看待這種關係?在影像中呈現這種關係有什麼困難嗎?
Fabrice Fouillet:要說人與他生活的環境之間的關係,其實是一種模糊的概念,但對我來講,這總是涉及在某一領土、團體或國家之內的社會和文化認同,正是這種文化的維度讓我感興趣,我也試圖讓拍攝計劃朝這個方向發展。人類與環境之間的關係是隨處可見的,即便沒必要遠離家鄉到很遠的地方去選有趣的主題,這個世界也是隨處都可以進行研究的。撇開影像和美學的層面不說,依我看來,難點在於敘述方式,而對待主題的方式跟主題本身一樣重要,我試著從總體結構上進行表達,而當問題出現時,這個結構可能會改變,而此時,編輯工作就至關重要了。
傅爾得:您能跟我們說說在拍巨型雕像系列時,發生的最奇幻或最有趣的事嗎?
Fabrice Fouillet:拍每一尊雕像都是一次不同的冒險,當我抵達目的地後,在看到雕像的第一眼時,那一瞬間總是令人非常激動,就像是多日旅行之後的一次小胜利般。發現新的文化是很值得的事,而每段旅行都會給我帶來很多的驚喜。我特別喜歡到中國和日本旅行,這是兩個我想要花很長時間去探索的國家。在運城拍關羽雕像的那次是我最美好的回憶之一,在晨霧中穿越那裡的常平村是一次非常超現實的經驗,那時,我在寂靜中孤身一人,因為霧氣,連雕像也無法看清,而當我繼續前行時,霧氣漸漸散去並為我開了路,最後,我發現了關羽雕像,它真令人驚嘆。當我爬上山到達雕像時,霧氣已經散開,而彼時陽光正燦爛。從村子走到雕像的那一程路,真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時刻。
–
Fabrice Fouillet
職業建築攝影師,生活於巴黎。其個人項目關注於身份的概念及人類與環境的密切關係。
–
本文刊載於《城市畫報》雜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