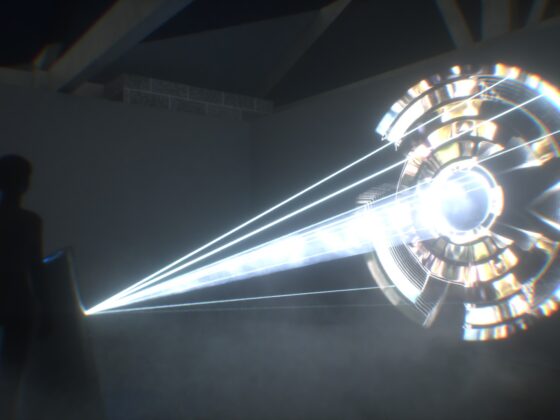網友點這張,這是布列松拍攝Giacometti跟他的作品。一開始我有點苦惱,因為這張照片可以談很多,譬如決定性瞬間,譬如藝術品的拍攝版權問題,又或是布列松與其藝術家朋友所反映的攝影師文化處境。我想談其中一小點,就是布列松的蒙太奇手法。在布列松之前,照片的背景就是背景,並沒有與照片的主體有等量齊觀的意義。
這很有可能是因為攝影的人習慣於把拍攝的對象當成作品的重心。
可是繪畫出身的布列松沒有這個概念,其實你看大部分有繪畫背景的攝影師都是這樣,他們並不是拍那個對象,而是經營整個畫面。
可是攝影的問題就是,畫面的經營並不是如繪畫隨心所欲,所以布列松必須花時間去尋找完整的構圖,然後等待主體走進那個視覺的戲劇性瞬間(不一定是事件的戲劇性瞬間)。
這就造成了布列松作品之中背景不再是背景,而像是另一張圖像。即使布列松沒有真的把兩張圖像拼接再一起,但是在概念上主體跟背景是當成兩張圖然後組成。
這樣做有什麼效果?
以這張照片為例,當然行走的雕像呼應行走的雕像很有趣,它在意象上與形式上都產生一種巧妙的關係。
但是蒙太奇真正的效果是,它讓拍攝的對象抽象化。因為布列松並不是經營一個生活場景,而是一個抽象化的圖示,這個圖示會讓處在其中的人也變得抽象,甚至具有超越日常的價值。
布列松之所以被稱讚賦予了小人物某種永恆性,就技術面來講其實就是把販夫走卒以蒙太奇的方式,放進了一個具有形式感的位置之中。
不過這也不是沒有代價的,這種蒙太奇式的肖像因為著重整體的構圖,所以主體本身的性格容易被掩蓋。
這不是比例上的問題,而是在概念上,布列松就是想要讓人置身在一個稍稍浮出現實的形式世界之中,好讓裡面的個人變成某種永恆的人,變成一種人的意象。
你看柯特茲拍人也是如此,裡面的人的面貌、個性都不重要,你只會記得反反覆覆有一個身穿大衣的中年男子,橫跨了幾十年的歲月,依然走在長椅的旁邊。
就這個意義上,布列松這張照片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它裡面就有一個抽象的人的雕像,還有一個具體的人,而前者是清晰地彷彿永遠存在,後者卻是模糊的、轉瞬即逝的,還有什麼比起這個更能夠代表現代主義攝影家對於人的看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