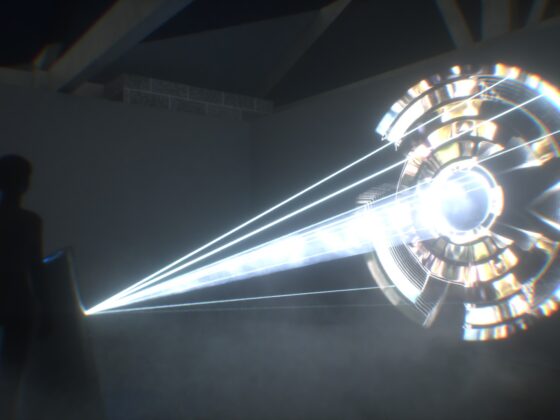這天下午下著大雨,剛結束在公司攝影課的我抱著筆電在大雨中奔跑,好不容易躲進一間全聯,但雨卻絲毫沒有要停歇的意思。狼狽地在全聯等到衣服稍微乾了一些,趁著一個雨勢漸小的時機,再奔跑到停車場,看著街上撐著傘的行人,對比抱著背包奔跑在雨中的自己,彷彿回到了大學時代。

photo by 鹿虹
鹿虹準備的投影片裡面有一張,寫著「不想長大」,面對正要社會化的年齡,才大四的他感到有些抗拒,就像他在面對整個城市,以及城市中川流不息的人群。
在開始講座前,我們坐在谷居一樓閒聊著,我突然被他帶入了那個年紀,他一邊在講著他的作品,我卻無法阻止自己掉入二十三歲那年的自己。

photo by 鹿虹
1976 的《撒野俱樂部》裡有一段歌
「有天變成了被對抗的大人
也別忘記今晚
我們帶群孩子闖進誰的殿堂
去撒泡尿 去撒撒野」
從什麼時候開始,我已經成為二十歲的我所瞧不起的世俗大人,我們會計較著觸及率,考量著業主的需求,煩惱著工作室的網路費。
而忘記了像個孩子般的在山上自在地拍照。

photo by 鹿虹
就像在對談最後,鹿虹提到我們可以透過瞭解藝術家的成長歷程,去窺探他作品的脈絡。而整晚的對談,我們跟隨著鹿虹的成長歷程,從擔任九五工作室的助理,拍了一些婚禮,在社區大學上著「普通」的攝影課,到大學的聯展,透過《Dobule》系列作品,利用鬥魚當作媒介,開始探索自己與影像之間的關係。
而在今年 Wonder Foto Day 上展出的《WILD WILD》,畫面越發的極簡,顯露出有點控制狂跟對齊強迫症的感覺,也連結到他自己對於生活的態度,例如皮包裡的零錢總是要整齊地讓孫文面對同一個方向。
讓人不禁期待他未來的作品,持續讓內心的自己擴張,總有一天會影響到世界的吧。

photo by 鹿虹
最後用鹿虹自己對於《WILD WILD》的敘述來作結:
「小時候對於生活的記憶已是都市化的景象,常聽父母親提及他們的兒時生活卻難以感同身受,那是一個回不去的年代吧!記得有一次從中部北上,在台北的捷運站裡清楚的感受到擁擠的人潮,卻感受不到自己的呼吸,對於這陌生,擦身而過的龐大流動感到不適甚至有些反胃,在穿梭的人群中無法再踏出步伐。後來我和友人一起逃到了大自然,在那裡,快門起落時彷彿切割出了一個場域,我清楚地感受到了自己的呼吸,感受到陽光的和煦,感受到所有一切包括自身的存在。」